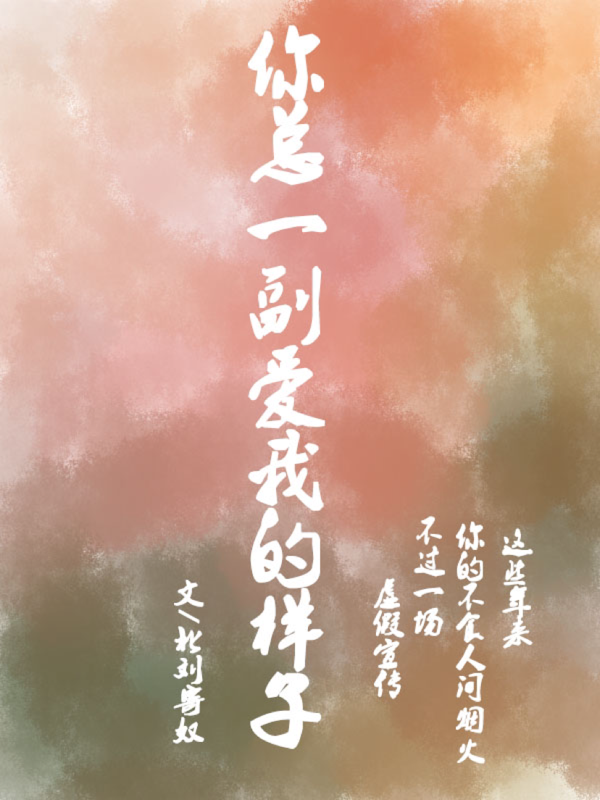{{ current.title }}
{{ chapter.title }}
章节已锁定,作者正在努力修改中
豆腐大家族迎来新成员豆花阅读APP,纯享耽美阅读体验,现在去各大应用商店下载,注册登录即送100多豆币。
文评
{{ novel.star}}分/{{novel.star_times}}人参与
评论
{{ novel.comment_times}}条
作者其他作品
推荐更多
-

被老皇帝强制后和他儿子在一起
乔熙十二岁那年因家乡发了洪水过不下去了进宫当了太监,后来被老皇帝看上,他心有不愿却也无可奈何,被折磨的体无完肤,后来机缘巧合之下与萧荣川心意相通,脱离苦海,同时萧荣川明白了权力的重要性,开始努力奋斗,最终二人一起奋斗走向人生巅峰 这是作者的第一本书啦,大家不要骂角色啊,也不要骂作者,谢谢啦,作者也不喜欢梦女之类的,但是应该也没人看我的书,看了也不要当角色梦女呀!!求求,毕竟我的书不要钱,感觉读起来不好及时弃文啊,大家不要骂我,如果是控控党的话就不要了吧,作者是坚定的cpj,所以小说对控控党可能不友好,权谋部分应该也不严谨,不要骂 受是真太监,但是只噶了蛋 攻是一个皇子,但是老皇帝不喜欢他,存在感很低 攻比较内敛,受很软又很刚 受和攻在一起后发奋学习,帮攻搞了好多次夫人外交 萧荣川是攻,乔熙是受 作者缘更哈 -

镜头之下
他是拥有百万粉丝的自由私fang摄影师,他是长相精致的高级修图师,两个人的碰撞,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

某种情感
“你玩够了没有,李承建?” “你把我们当什么了?……无论是你小时候突然孤立我,还是把田林当成林熏的替代品,你都不觉得你这样做很恶心么?” “只因为你喜欢林熏,就把我对你的友情,把田林对你的感情,都当成玩具一样儿戏的对待。你实在是,令我厌恶。” 面对戴小直咄咄逼人的态度,陆清以沉默应对。 一场意外,致使两个童年玩伴的心中产生隔阂。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渐渐浮出水面。 那一年的夏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

我的心好累
女主叫孙糯凝 出生于世家 自身会棋琴书画 可是却嫁给了一个落魄皇子 但是她陪着顾川涯一步步登上高天却落了个惨死 女 芳龄18 男主顾川涯 出生于皇宫 自小母亲不待见他 还是个落魄皇子 母妃也不受宠 后来芳龄16遇到一个温婉女子 却最后亲手将她抛弃 男 芳龄18 -

江山策
「炙热赤诚侯爷攻」×「一心为民皇子受」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泰安国、旭国、兰国分而治之于天下。 他们为地盘之事纷争不断,北边更有十二部虎视眈眈。 冷冥璃原本是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却一朝穿越成泰安国的侯爷冷冥璃,他原本怀揣着赤诚热烈的心打算轰轰烈烈可以青史留名的事情,但是却发现这个世界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 就单单的一个皇权猜疑变压的他喘不过气来。 赏花宴中皇帝为了打压冷冥璃,把自己最不受宠的皇子南宫泽嫁给了冷冥璃。 在日渐的相处的过程之中冷冥璃发现眼前这个不受宠的地坤才是皇室之中最重情的,才是最一心为民的。 -

【快穿】恋爱脑养成系统
贺延是个无性恋。 无欲无求二十多年,一朝被劈死。 奈何桥边喜提『Cosplay恋爱脑』系统。 “扮恋爱脑走剧情,集点换取复活卡!” 贺延:扮演恋爱脑?手拿把掐! 谁说无性恋不能拿恋爱剧本? 请看无情者如何拿捏有情人! -

【薰嗣】illusion forever
空白的十四年所发生的事。纯属虚构。ooc致歉。 -

昭然寻觅
“到底在哪?你在哪?你在哪?”“自从那次断了联系之后,命魂牌就灭了。所以到底在哪?发生了什么?是谁害了你?”花梨一遍一遍的反问思考,没有人能回答她的问题。对于一起长大的姐姐花梨的内心是极为复杂的,姐姐从她十三岁就去闯荡,留她一个人守护在那方寸之地。外面的世界总是让人眼花缭乱,就连姐姐也没能逃脱。一离开就是五年,上次联系说不久就会带着自己的心上人回家,没过多久就香消玉殒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花梨为了寻找姐姐并查找原因,出了自己守护了五年的地方,但却像无头苍蝇,不知该向何处寻找。 -

小师弟今天也在修罗场求生
他是剑霄阁最年轻的首席弟子,白衣胜雪,剑光如霜,万人敬仰的白师兄,却唯独对小师弟书执念成狂。 他是玄机门最不羁的少年天才,黑衣如夜,桀骜不驯,自幼相伴的黑师兄,却唯独对小师弟展现柔情。 何为冷酷的执念,何为嬉笑的真心。 卦象推演出灭门之兆,却算不出这场情劫的因果。 —————————————— 好久没有发文了,新坑还要挑战古风,依旧是慢热的类型,希望能有小可爱捧场🤗 -

当戏精遇上对手
一个富二代少爷整天觉得自己活在书里,觉得自己身为豪门少爷一定会家道中落,然后跟一个表面不和的男人联姻的。为此他每天都蹲在他爹下班后门口,两眼欲穿等着自家公司倒闭的消息。 直到某天真的传来噩耗……
下载APP,查看更多精彩内容